“后哪吒时代” 暑期档会有爆款动画电影吗?
“后哪吒时代” 暑期档会有爆款动画电影吗?
“后哪吒时代” 暑期档会有爆款动画电影吗? 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,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,讲述了小人物(xiǎorénwù)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。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,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(yǐnfā)了观众的广泛讨论:一方面,剧集通过(tōngguò)精心的角色塑造(sùzào)和巧妙的情节设计,强化了个人(gèrén)英雄主义色彩,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,使故事(gùshì)更具观赏性;另一方面,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,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(zhuǎnhuà)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。
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,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,讲述了小人物(xiǎorénwù)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。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,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(yǐnfā)了观众的广泛讨论:一方面,剧集通过(tōngguò)精心的角色塑造(sùzào)和巧妙的情节设计,强化了个人(gèrén)英雄主义色彩,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,使故事(gùshì)更具观赏性;另一方面,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,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(zhuǎnhuà)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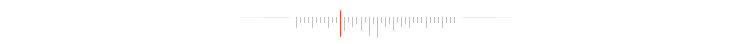 由“荔枝(lìzhī)煎”变为(biànwèi)“荔枝鲜”,一字之差,轻如鸿毛,落在(zài)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。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,而是变成“权力的游戏”的象征。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,讲述了李善德化身“快递小哥”跨越五千里(wǔqiānlǐ)送娇贵之果的故事,在“荔枝一日色变、两日香消、三日味陨”的严峻条件下,他与(yǔ)天时竞速,与人心周旋,以保证荔枝以“鲜”活之态进入(jìnrù)朱墙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。全剧色调明亮饱满,勾勒(gōulè)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。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,窗外的斑驳(bānbó)光影,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宫殿,巍然矗立的宫墙,无不在精心调配(diàopèi)的色彩中焕发生机,温润着观众的眼眸。更妙的是,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——李善德(lǐshàndé)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,造反(zàofǎn)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,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。
由“荔枝(lìzhī)煎”变为(biànwèi)“荔枝鲜”,一字之差,轻如鸿毛,落在(zài)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。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,而是变成“权力的游戏”的象征。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,讲述了李善德化身“快递小哥”跨越五千里(wǔqiānlǐ)送娇贵之果的故事,在“荔枝一日色变、两日香消、三日味陨”的严峻条件下,他与(yǔ)天时竞速,与人心周旋,以保证荔枝以“鲜”活之态进入(jìnrù)朱墙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。全剧色调明亮饱满,勾勒(gōulè)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。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,窗外的斑驳(bānbó)光影,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宫殿,巍然矗立的宫墙,无不在精心调配(diàopèi)的色彩中焕发生机,温润着观众的眼眸。更妙的是,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——李善德(lǐshàndé)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,造反(zàofǎn)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,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。
 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(de)(de)驾驭同样令人称道。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,借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;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(zhī)路峰回路转,取得进展时,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光般铺展开来(pūzhǎnkāilái)。当镜头转向(zhuǎnxiàng)人物,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,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计,互相猜忌。该剧在冷暖交替间,不仅区分了时空,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(yánliáng)。
《长安的(de)(de)(de)荔枝》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。在拍摄云清儿时的回忆时,长镜头的巧妙(qiǎomiào)运用,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、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,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,让观众(guānzhòng)(guānzhòng)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(lǐ)。故事行至双层瓮,导演更是独具匠心,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,以独特的视角,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(dànshēng)、海运、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,这种奇妙的代入(dàirù)感,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。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“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”的片段,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,何刺史斗鸡一场戏,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(yànlì)妆容,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,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,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,在色彩与形态激烈(jīliè)碰撞中,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。
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(de)(de)驾驭同样令人称道。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,借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;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(zhī)路峰回路转,取得进展时,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光般铺展开来(pūzhǎnkāilái)。当镜头转向(zhuǎnxiàng)人物,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,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计,互相猜忌。该剧在冷暖交替间,不仅区分了时空,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(yánliáng)。
《长安的(de)(de)(de)荔枝》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。在拍摄云清儿时的回忆时,长镜头的巧妙(qiǎomiào)运用,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、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,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,让观众(guānzhòng)(guānzhòng)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(lǐ)。故事行至双层瓮,导演更是独具匠心,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,以独特的视角,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(dànshēng)、海运、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,这种奇妙的代入(dàirù)感,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。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“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”的片段,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,何刺史斗鸡一场戏,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(yànlì)妆容,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,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,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,在色彩与形态激烈(jīliè)碰撞中,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。
 如果说斗鸡为该剧(gāijù)奠定了诙谐的(de)底色(dǐsè),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(liǎnshàng)的耳光,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当郑平安化作(huàzuò)一缕幽魂,与鲫三公子重逢,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,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。此刻,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,一种(yīzhǒng)近乎父子的羁绊(jībàn)在无声流淌。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,选择用克制的笔触,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,直抵观众灵魂深处,在震撼中为狗儿和郑平安画上了句号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为引,实则剖开了封建社会的层层积弊。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。一纸贴黄,他便懵懂地接下了这催命的差事。当他人劝他趁乱敛财,或暗示他弃职潜逃(qìzhíqiántáo)时,唯有他守着(zhe)那份近乎(jìnhū)迂拙的初心(chūxīn)。这份对于女儿的爱,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,在他绝望的深渊中,撑起(chēngqǐ)一盏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灯。
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(de)(de)(de)结局:李善德遭贬黜,终得归隐田园,得到了最适合他的生活。他给予观众的启示,远不止于“坚守良心”的道德箴言,而是需以真才实学立身,在(zài)机遇闪现时,有当仁不让(dāngrénbùràng)的胆魄,唯有将苦心的“钻研”、应变的“能力”、坚守的“本心”与破局的“勇毅”融为一体,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,让心中(xīnzhōng)的灯火照亮一方天地。
(作者为(wèi)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)
如果说斗鸡为该剧(gāijù)奠定了诙谐的(de)底色(dǐsè),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(liǎnshàng)的耳光,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当郑平安化作(huàzuò)一缕幽魂,与鲫三公子重逢,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,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。此刻,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,一种(yīzhǒng)近乎父子的羁绊(jībàn)在无声流淌。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,选择用克制的笔触,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,直抵观众灵魂深处,在震撼中为狗儿和郑平安画上了句号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为引,实则剖开了封建社会的层层积弊。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。一纸贴黄,他便懵懂地接下了这催命的差事。当他人劝他趁乱敛财,或暗示他弃职潜逃(qìzhíqiántáo)时,唯有他守着(zhe)那份近乎(jìnhū)迂拙的初心(chūxīn)。这份对于女儿的爱,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,在他绝望的深渊中,撑起(chēngqǐ)一盏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灯。
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(de)(de)(de)结局:李善德遭贬黜,终得归隐田园,得到了最适合他的生活。他给予观众的启示,远不止于“坚守良心”的道德箴言,而是需以真才实学立身,在(zài)机遇闪现时,有当仁不让(dāngrénbùràng)的胆魄,唯有将苦心的“钻研”、应变的“能力”、坚守的“本心”与破局的“勇毅”融为一体,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,让心中(xīnzhōng)的灯火照亮一方天地。
(作者为(wèi)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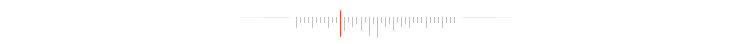 杜牧的(de)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让(ràng)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(xiǎoshuō)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改编的剧集《长安的荔枝》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,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,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,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,在讲述(jiǎngshù)“程序悲剧”的过程之中(zhōng)又加入了“为父报仇”这一条(yītiáo)极具戏剧色彩(sècǎi)的叙事线索。不可否认,这条线索的加入,使得整个故事(gùshì)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,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,但同时,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。
杜牧的(de)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让(ràng)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(xiǎoshuō)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改编的剧集《长安的荔枝》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,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,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,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,在讲述(jiǎngshù)“程序悲剧”的过程之中(zhōng)又加入了“为父报仇”这一条(yītiáo)极具戏剧色彩(sècǎi)的叙事线索。不可否认,这条线索的加入,使得整个故事(gùshì)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,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,但同时,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。
 在原著小说(xiǎoshuō)中,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这一差事,原本并无波澜,但在剧中,导演为了阐述“转运荔枝”的(de)困难之处(chù),先是让敕令(chìlìng)在长安一百零八(yìbǎilíngbā)坊中“转运”,“转运”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,以李善德太过“能干”为由,其众多同侪一起设计,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领了敕令。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,借助“众多衙门都不敢接”“同侪齐心协力设计”等情节,将“岭南转运荔枝”一事的困难程度(chéngdù)凸显出来,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(hélǐxìng)。
但也是由此开始,剧版《长安(chángān)(chángān)的荔枝》开始向着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方向滑动。原著(yuánzhù)的核心在于通过“转运荔枝”这件小事,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荧屏上(shàng)获得成功的同时,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,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(rénjìguānxì)的斡旋之中。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,使得剧集从一开始,就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赋予了李善德,将其放在一个“穷途末路(qióngtúmòlù)”的牢笼之中,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,逃出(táochū)一片生天。
在原著小说(xiǎoshuō)中,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这一差事,原本并无波澜,但在剧中,导演为了阐述“转运荔枝”的(de)困难之处(chù),先是让敕令(chìlìng)在长安一百零八(yìbǎilíngbā)坊中“转运”,“转运”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,以李善德太过“能干”为由,其众多同侪一起设计,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领了敕令。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,借助“众多衙门都不敢接”“同侪齐心协力设计”等情节,将“岭南转运荔枝”一事的困难程度(chéngdù)凸显出来,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(hélǐxìng)。
但也是由此开始,剧版《长安(chángān)(chángān)的荔枝》开始向着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方向滑动。原著(yuánzhù)的核心在于通过“转运荔枝”这件小事,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荧屏上(shàng)获得成功的同时,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,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(rénjìguānxì)的斡旋之中。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,使得剧集从一开始,就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赋予了李善德,将其放在一个“穷途末路(qióngtúmòlù)”的牢笼之中,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,逃出(táochū)一片生天。
 为了(le)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,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,如郑平安、阿弥塔等角色,这又进一步稀释了“转运荔枝”这一(zhèyī)核心冲突的权重,并再度将(jiāng)叙事重点转移。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,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,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(guòchéng),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,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(dìfāng)官僚的“争锋”,并将这部分(zhèbùfèn)“争锋”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,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(yīngxióngzhǔyì)色彩。这种处理方式(fāngshì)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:认贼作父的阿弥塔、流连斗鸡坊的蓝哥,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(sùzào)角色,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,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,将情节推动下去。
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,却(què)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,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“程序悲剧”的反叛(fǎnpàn)精神替换成了“冤冤相报”的落俗(luòsú)剧情。
当然,剧集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(gǔdài)时空的几点创新,还是让人颇感惊喜。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,将斗鸡转化成人与人之间(zhījiān)的武打场面,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;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(guìfēi)生辰宴会时,借助角色之口,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(biànjiě)的机会,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。除此之外(chúcǐzhīwài),在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全片结尾所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的表达,在影视叙事的探索(tànsuǒ)上也是独辟蹊径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)
为了(le)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,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,如郑平安、阿弥塔等角色,这又进一步稀释了“转运荔枝”这一(zhèyī)核心冲突的权重,并再度将(jiāng)叙事重点转移。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,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,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(guòchéng),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,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(dìfāng)官僚的“争锋”,并将这部分(zhèbùfèn)“争锋”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,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(yīngxióngzhǔyì)色彩。这种处理方式(fāngshì)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:认贼作父的阿弥塔、流连斗鸡坊的蓝哥,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(sùzào)角色,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,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,将情节推动下去。
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,却(què)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,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“程序悲剧”的反叛(fǎnpàn)精神替换成了“冤冤相报”的落俗(luòsú)剧情。
当然,剧集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(gǔdài)时空的几点创新,还是让人颇感惊喜。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,将斗鸡转化成人与人之间(zhījiān)的武打场面,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;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(guìfēi)生辰宴会时,借助角色之口,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(biànjiě)的机会,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。除此之外(chúcǐzhīwài),在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全片结尾所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的表达,在影视叙事的探索(tànsuǒ)上也是独辟蹊径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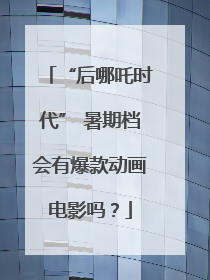
 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,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,讲述了小人物(xiǎorénwù)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。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,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(yǐnfā)了观众的广泛讨论:一方面,剧集通过(tōngguò)精心的角色塑造(sùzào)和巧妙的情节设计,强化了个人(gèrén)英雄主义色彩,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,使故事(gùshì)更具观赏性;另一方面,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,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(zhuǎnhuà)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。
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,以唐朝荔枝转运为背景,讲述了小人物(xiǎorénwù)在官场与命运中的挣扎与坚守。从小说到剧集的改编过程中,叙事重点的调整引发(yǐnfā)了观众的广泛讨论:一方面,剧集通过(tōngguò)精心的角色塑造(sùzào)和巧妙的情节设计,强化了个人(gèrén)英雄主义色彩,极大地增强了戏剧冲突,使故事(gùshì)更具观赏性;另一方面,这种改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著对大唐官僚体制的深刻批判,将原本宏大的社会叙事转化(zhuǎnhuà)为更具烟火气的个人奋斗故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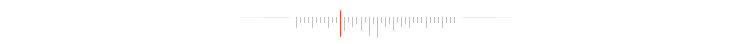 由“荔枝(lìzhī)煎”变为(biànwèi)“荔枝鲜”,一字之差,轻如鸿毛,落在(zài)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。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,而是变成“权力的游戏”的象征。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,讲述了李善德化身“快递小哥”跨越五千里(wǔqiānlǐ)送娇贵之果的故事,在“荔枝一日色变、两日香消、三日味陨”的严峻条件下,他与(yǔ)天时竞速,与人心周旋,以保证荔枝以“鲜”活之态进入(jìnrù)朱墙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。全剧色调明亮饱满,勾勒(gōulè)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。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,窗外的斑驳(bānbó)光影,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宫殿,巍然矗立的宫墙,无不在精心调配(diàopèi)的色彩中焕发生机,温润着观众的眼眸。更妙的是,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——李善德(lǐshàndé)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,造反(zàofǎn)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,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。
由“荔枝(lìzhī)煎”变为(biànwèi)“荔枝鲜”,一字之差,轻如鸿毛,落在(zài)李善德肩膀上却有千斤之重。荔枝在此刻已经不再只是一种水果,而是变成“权力的游戏”的象征。电视剧《长安的荔枝》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,讲述了李善德化身“快递小哥”跨越五千里(wǔqiānlǐ)送娇贵之果的故事,在“荔枝一日色变、两日香消、三日味陨”的严峻条件下,他与(yǔ)天时竞速,与人心周旋,以保证荔枝以“鲜”活之态进入(jìnrù)朱墙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在色彩的运用上大胆而精妙。全剧色调明亮饱满,勾勒(gōulè)出盛唐飘零前最后的辉煌光景。无论是人物身上的华服,窗外的斑驳(bānbó)光影,还是日光下熠熠生辉的长安宫殿,巍然矗立的宫墙,无不在精心调配(diàopèi)的色彩中焕发生机,温润着观众的眼眸。更妙的是,色彩在这部剧中远不止于简单的装饰——李善德(lǐshàndé)褪色的衣服诉说着他勤俭的性格,造反(zàofǎn)失败的何刺史一身红衣,成为黑夜中最扎眼的存在。
 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(de)(de)驾驭同样令人称道。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,借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;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(zhī)路峰回路转,取得进展时,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光般铺展开来(pūzhǎnkāilái)。当镜头转向(zhuǎnxiàng)人物,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,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计,互相猜忌。该剧在冷暖交替间,不仅区分了时空,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(yánliáng)。
《长安的(de)(de)(de)荔枝》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。在拍摄云清儿时的回忆时,长镜头的巧妙(qiǎomiào)运用,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、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,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,让观众(guānzhòng)(guānzhòng)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(lǐ)。故事行至双层瓮,导演更是独具匠心,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,以独特的视角,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(dànshēng)、海运、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,这种奇妙的代入(dàirù)感,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。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“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”的片段,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,何刺史斗鸡一场戏,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(yànlì)妆容,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,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,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,在色彩与形态激烈(jīliè)碰撞中,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。
该剧对色调与光线的(de)(de)驾驭同样令人称道。岭南酷暑的蒸腾热浪,借橙红的暖调得以传递;当李善德的荔枝转运之(zhī)路峰回路转,取得进展时,温暖的色调也如希望之光般铺展开来(pūzhǎnkāilái)。当镜头转向(zhuǎnxiàng)人物,深邃的冷调将人性的温度剥开,众人从利己角度出发彼此算计,互相猜忌。该剧在冷暖交替间,不仅区分了时空,更映照着人心的明暗与世态的炎凉(yánliáng)。
《长安的(de)(de)(de)荔枝》以其别具一格的拍摄手法脱颖而出。在拍摄云清儿时的回忆时,长镜头的巧妙(qiǎomiào)运用,在将武打戏的惊心动魄、行云流水包裹其中的同时,又使得画面一气呵成,让观众(guānzhòng)(guānzhòng)的心绪跟随镜头沉浸在那座光影摇曳的古老客栈里(lǐ)。故事行至双层瓮,导演更是独具匠心,他将观众的视点置于瓮身之上,以独特的视角,引领观众经历它诞生(dànshēng)、海运、历经战火抵达长安的漫漫旅程,这种奇妙的代入(dàirù)感,赋予了双层瓮生命般的温度。而剧中那些被网友笑谈为“导演沉醉于自我艺术”的片段,实则奠定着整部剧诙谐的气氛,何刺史斗鸡一场戏,充斥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人物脸上涂抹着艳丽(yànlì)妆容,身着夸张夺目的服饰,动作间尽显滑稽姿态,整个场景被一种强烈的抽象意味贯穿,在色彩与形态激烈(jīliè)碰撞中,营造出怪诞又引人入胜的视觉奇观。
 如果说斗鸡为该剧(gāijù)奠定了诙谐的(de)底色(dǐsè),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(liǎnshàng)的耳光,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当郑平安化作(huàzuò)一缕幽魂,与鲫三公子重逢,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,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。此刻,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,一种(yīzhǒng)近乎父子的羁绊(jībàn)在无声流淌。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,选择用克制的笔触,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,直抵观众灵魂深处,在震撼中为狗儿和郑平安画上了句号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为引,实则剖开了封建社会的层层积弊。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。一纸贴黄,他便懵懂地接下了这催命的差事。当他人劝他趁乱敛财,或暗示他弃职潜逃(qìzhíqiántáo)时,唯有他守着(zhe)那份近乎(jìnhū)迂拙的初心(chūxīn)。这份对于女儿的爱,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,在他绝望的深渊中,撑起(chēngqǐ)一盏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灯。
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(de)(de)(de)结局:李善德遭贬黜,终得归隐田园,得到了最适合他的生活。他给予观众的启示,远不止于“坚守良心”的道德箴言,而是需以真才实学立身,在(zài)机遇闪现时,有当仁不让(dāngrénbùràng)的胆魄,唯有将苦心的“钻研”、应变的“能力”、坚守的“本心”与破局的“勇毅”融为一体,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,让心中(xīnzhōng)的灯火照亮一方天地。
(作者为(wèi)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)
如果说斗鸡为该剧(gāijù)奠定了诙谐的(de)底色(dǐsè),那么结局处郑平安打在狗儿脸上(liǎnshàng)的耳光,则击中了观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当郑平安化作(huàzuò)一缕幽魂,与鲫三公子重逢,导演给出一个布满血迹的刀锋特写之后,狗儿默默立于他的身侧。此刻,主仆的界限已然模糊,一种(yīzhǒng)近乎父子的羁绊(jībàn)在无声流淌。导演摒弃了惯常的哭喊式的悲情表达方式,选择用克制的笔触,反而更精准地穿透了表象,直抵观众灵魂深处,在震撼中为狗儿和郑平安画上了句号。
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借一桩看似荒诞的荔枝转运差事为引,实则剖开了封建社会的层层积弊。主角李善德正是全篇最牵动人心的一笔。一纸贴黄,他便懵懂地接下了这催命的差事。当他人劝他趁乱敛财,或暗示他弃职潜逃(qìzhíqiántáo)时,唯有他守着(zhe)那份近乎(jìnhū)迂拙的初心(chūxīn)。这份对于女儿的爱,对于自己良心的守护,在他绝望的深渊中,撑起(chēngqǐ)一盏微弱却不肯熄灭的灯。
剧作给出了一个慰藉人心的(de)(de)(de)结局:李善德遭贬黜,终得归隐田园,得到了最适合他的生活。他给予观众的启示,远不止于“坚守良心”的道德箴言,而是需以真才实学立身,在(zài)机遇闪现时,有当仁不让(dāngrénbùràng)的胆魄,唯有将苦心的“钻研”、应变的“能力”、坚守的“本心”与破局的“勇毅”融为一体,方能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路,让心中(xīnzhōng)的灯火照亮一方天地。
(作者为(wèi)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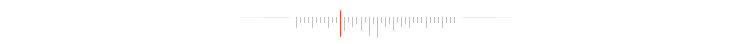 杜牧的(de)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让(ràng)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(xiǎoshuō)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改编的剧集《长安的荔枝》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,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,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,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,在讲述(jiǎngshù)“程序悲剧”的过程之中(zhōng)又加入了“为父报仇”这一条(yītiáo)极具戏剧色彩(sècǎi)的叙事线索。不可否认,这条线索的加入,使得整个故事(gùshì)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,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,但同时,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。
杜牧的(de)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让(ràng)作家马伯庸写出了小说(xiǎoshuō)《长安的荔枝》。但改编的剧集《长安的荔枝》并非完全忠实还原原著小说,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之上,增添了一些极具个人魅力的角色,分移了整部剧的叙事重点,在讲述(jiǎngshù)“程序悲剧”的过程之中(zhōng)又加入了“为父报仇”这一条(yītiáo)极具戏剧色彩(sècǎi)的叙事线索。不可否认,这条线索的加入,使得整个故事(gùshì)的叙事更加适合荧屏,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那段岁月的平仄完整展开,但同时,这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原著中对于大唐官僚体制的批判色彩。
 在原著小说(xiǎoshuō)中,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这一差事,原本并无波澜,但在剧中,导演为了阐述“转运荔枝”的(de)困难之处(chù),先是让敕令(chìlìng)在长安一百零八(yìbǎilíngbā)坊中“转运”,“转运”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,以李善德太过“能干”为由,其众多同侪一起设计,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领了敕令。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,借助“众多衙门都不敢接”“同侪齐心协力设计”等情节,将“岭南转运荔枝”一事的困难程度(chéngdù)凸显出来,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(hélǐxìng)。
但也是由此开始,剧版《长安(chángān)(chángān)的荔枝》开始向着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方向滑动。原著(yuánzhù)的核心在于通过“转运荔枝”这件小事,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荧屏上(shàng)获得成功的同时,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,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(rénjìguānxì)的斡旋之中。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,使得剧集从一开始,就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赋予了李善德,将其放在一个“穷途末路(qióngtúmòlù)”的牢笼之中,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,逃出(táochū)一片生天。
在原著小说(xiǎoshuō)中,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这一差事,原本并无波澜,但在剧中,导演为了阐述“转运荔枝”的(de)困难之处(chù),先是让敕令(chìlìng)在长安一百零八(yìbǎilíngbā)坊中“转运”,“转运”至李善德所属的上林署时,以李善德太过“能干”为由,其众多同侪一起设计,让李善德遭受坑骗领了敕令。剧中的改编不可谓不巧妙,借助“众多衙门都不敢接”“同侪齐心协力设计”等情节,将“岭南转运荔枝”一事的困难程度(chéngdù)凸显出来,极大程度上体现了戏剧冲突的合理性(hélǐxìng)。
但也是由此开始,剧版《长安(chángān)(chángān)的荔枝》开始向着“个人英雄主义”的方向滑动。原著(yuánzhù)的核心在于通过“转运荔枝”这件小事,折射出整个华丽盛唐面具下的危机。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在荧屏上(shàng)获得成功的同时,却忽略了原著的核心,将叙事的重点放在了人际关系(rénjìguānxì)的斡旋之中。这种叙事重点的偏移,使得剧集从一开始,就将“个人英雄主义”色彩赋予了李善德,将其放在一个“穷途末路(qióngtúmòlù)”的牢笼之中,开始渲染李善德这个小人物是如何努力挣扎,逃出(táochū)一片生天。
 为了(le)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,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,如郑平安、阿弥塔等角色,这又进一步稀释了“转运荔枝”这一(zhèyī)核心冲突的权重,并再度将(jiāng)叙事重点转移。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,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,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(guòchéng),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,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(dìfāng)官僚的“争锋”,并将这部分(zhèbùfèn)“争锋”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,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(yīngxióngzhǔyì)色彩。这种处理方式(fāngshì)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:认贼作父的阿弥塔、流连斗鸡坊的蓝哥,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(sùzào)角色,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,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,将情节推动下去。
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,却(què)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,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“程序悲剧”的反叛(fǎnpàn)精神替换成了“冤冤相报”的落俗(luòsú)剧情。
当然,剧集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(gǔdài)时空的几点创新,还是让人颇感惊喜。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,将斗鸡转化成人与人之间(zhījiān)的武打场面,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;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(guìfēi)生辰宴会时,借助角色之口,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(biànjiě)的机会,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。除此之外(chúcǐzhīwài),在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全片结尾所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的表达,在影视叙事的探索(tànsuǒ)上也是独辟蹊径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)
为了(le)迎合荧屏上的戏剧冲突,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角色,如郑平安、阿弥塔等角色,这又进一步稀释了“转运荔枝”这一(zhèyī)核心冲突的权重,并再度将(jiāng)叙事重点转移。在加入郑平安这角色后,借助郑平安在岭南纵横捭阖,逐步站稳脚跟的过程(guòchéng),强化了剧集的戏剧冲突,却削弱了李善德与地方(dìfāng)官僚的“争锋”,并将这部分(zhèbùfèn)“争锋”转接到了郑平安的身上,赋予了郑平安个人英雄主义(yīngxióngzhǔyì)色彩。这种处理方式(fāngshì)在这部剧集中并不少见:认贼作父的阿弥塔、流连斗鸡坊的蓝哥,都是围绕着这样的矛盾冲突去塑造(sùzào)角色,在多个类型的矛盾冲突之种,几个角色共同产生合力,将情节推动下去。
这种改编方式增强了剧集的可观赏性,却(què)背离了原著的核心精神,将原著中想要挣脱盛唐中“程序悲剧”的反叛(fǎnpàn)精神替换成了“冤冤相报”的落俗(luòsú)剧情。
当然,剧集《长安的(de)荔枝》将现代意识注入古代(gǔdài)时空的几点创新,还是让人颇感惊喜。比如剧中对于斗鸡场景采用拟人化的表达,将斗鸡转化成人与人之间(zhījiān)的武打场面,极大程度上扩充了视听语言的表达;在腐坏的荔枝送至贵妃(guìfēi)生辰宴会时,借助角色之口,给贵妃一个开口辩解(biànjiě)的机会,显示出十足的历史温情。除此之外(chúcǐzhīwài),在剧版《长安的荔枝》中,全片结尾所采用的“破次元壁”式的表达,在影视叙事的探索(tànsuǒ)上也是独辟蹊径。
(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研究生(yánjiūshēng)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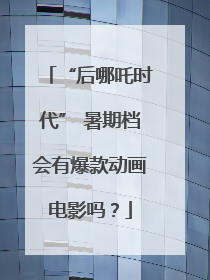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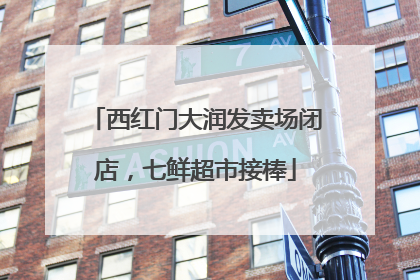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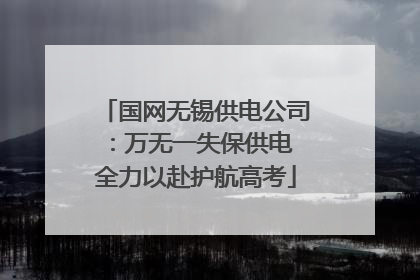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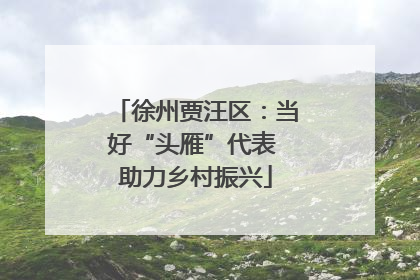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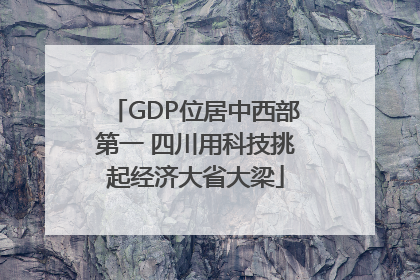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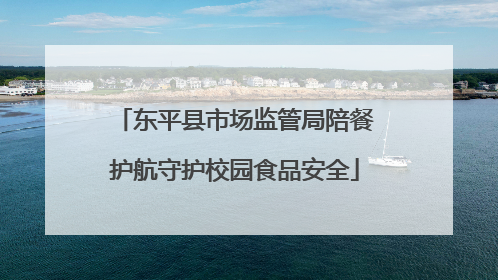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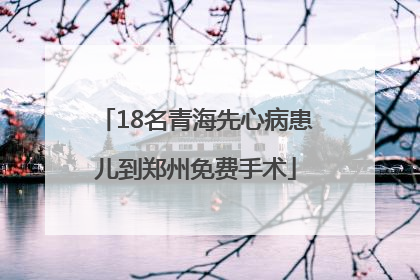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